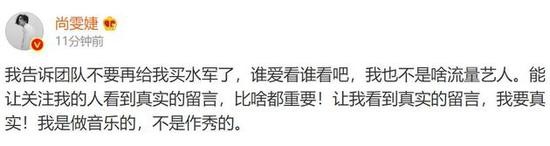一位永远定格在25岁的战地记者。
一位家境富足却放弃温柔乡,孤身一人,出生入死,在抗战前线记录新闻的记者。
一位充满家国情怀、充满理想与激情、才华横溢的记者。
一位中国的卡帕。
……
真的很惭愧,作为军事记者,很多年里我竟不知道方大曾。可能就是因为他生命太短暂了,短得如一道闪电倏然划过历史夜空,以至于中国新闻史都来不及充分记录。抑或是他神秘消失在上个世纪30年代抗战的硝烟里,留下了至今未破解的一个谜。好在今天的新闻同仁们踏上了寻找小方的长路,使小方的身影在我们眼中越来越清晰了。
我先是在《范长江文集》里读到《忆小方》,知道了这个名字,之后在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时,看了电视纪录片《一份报纸的抗战》,和冯雪松的专著《方大曾:消失与重现》,有了对小方这位新闻前辈直观而强烈的印象。然后回过头去追读他珍贵的新闻通讯,去看他拍摄的照片,去读今天的新闻人为寻找和纪念他而写下的各类文字。汇集起来的感受就是:震撼,一位伟岸的新闻英雄!
新闻易碎吗?70多年过去了,在今天的信息爆炸时代,回看当年小方的新闻作品,竟然还是那么新鲜。例如1937年8月南口之战的一篇现场报道:“……十二日早晨,三十多辆坦克车驶入了南口。应验了美国武官给我们的忠告,坦克车简直是“铁怪”,三英寸厚的钢壳,什么也打不透它。重炮打中了它,最多不过打一个翻身,然后它又会自己把自己调整过来继续行驶。只要有一道山沟,它就沿隙而上,怎么奈何它呢?办法是有的,第七连连长带着两排人跳出阵地冲向坦克车去,他们冲到这“铁怪”的跟前,铁怪自然少不了有好多窗口以备里面的人向外射击之用,于是大家就不顾一切的攀上前去,把手榴弹往窗口里丢,用手枪伸进去打,以血肉和钢铁搏斗,铁怪不支了,居然败走,并且其中的六辆因为里面的人全都死了,所以就成了我们的战利品,两排勇敢的健儿虽然死了一半,但我们终于获得胜利,坦克车没有人能驾驶,而又没有那样大的炸弹或地雷能将它毁掉,结果这六辆宝贵的玩艺儿,在我们阵地里放了两天,终归又被敌人用新的坦克车拖了回去……”,文字很轻松,但能感受到战斗的惨烈。他的新闻通讯并不多,目前找到的一共27篇,都来自抗战前线,篇篇详尽扎实,真切生动,最珍贵的是那些细节描写,读来如身临其境。
小方长于摄影,相机与笔是他手中并行的两件武器。他留在家中被他妹妹保存下来的底片编号有1200张,全部纪实照片,其中多是抗战题材。许多发表在北平的《世界画报》上,也在当时的影展展出。大多数内容是底层穷苦劳动者,如人力车夫、纤夫、矿工、赶毛驴的农民、快饿死的孩子,传递着多难中国的现实,让全国乃至全世界都看到日寇铁蹄践踏下的中国现状。同时还有中国军队官兵在战壕中作,硝烟弥漫的战斗场面,游行、集会中的学生和革命者……从各个层面与角度纪录了中国人民不屈的抗战。
这些作品今天来看,照样引人入胜。每篇通讯,每幅照片,都是中国抗战初期最具体而真实的历史回放,年代越久远,越感受到其价值的永恒。并且当我们同时翻看他的新闻通讯与图片,会感到十分惊异,那时的小方就有了今天全媒体时代的新闻理念:有图有真相。
走近小方,近到熟悉小方的音容笑貌,像是自己的亲人。对于我之倍觉亲近,还有一层个人的情感 — 我父亲也曾是军事记者,战争年代也曾在前沿战壕里采写浴血将士。只是全国解放后大多时间他不再从事新闻工作,而且年逾古稀患了阿尔茨海默症,记忆被强行删除,待我渴望知道父亲曾经的经历时,已经永远失去了与他交流的机会。好在父亲留下了战争年代的日记和后来回忆的散文,从那些娟秀细密的字体间,那份厚重的文学底韵、真诚的情感和严谨的思维中,我能看到他与小方共同的文风,共同的情怀与品质。
这也许是我热爱军事新闻工作的基因始然,也是我在阅读小方时,仿佛看到了自己的父亲。
我参加过决战非典的一线报道,非典最恐怖的日子我进入309医院非典重症病区;参加过汶川大地震救灾一线报道,在能见度极低的气象条件下,随直升机组强飞唐家山;再之前的之前,年轻的我在中越边境自卫还击战前线采写报告文学……所有这些经历过程我没有害怕只觉得热血沸腾。我后来在荣获中国新闻大奖的颁奖会上发言的主题是“抵近前沿”,自视作为记者已然合格。
如今想来,和小方比,算什么呢!今天的我们无冻饿之虞,有交通保障,有组织做后盾,有便利的通讯工具,偶有危险也终是无恙。重要的是身为军事记者的我不曾经历战火的洗礼,没有加入过“战地记者”行列,是为硬伤。
而小方不是军人,却出入枪林弹雨,贴近底层民众生活,不记生活的极端艰苦,置身每一刻的生死危难,很多情况下没有人委派他任务。他凭着理想信念,凭着一腔爱国情怀,始终充满激情地、用高贵的职业精神去记录、记录,不论文字还是照片,无一不是用生命、鲜血、胆识和勇气换来。美国新闻媒体自述作家Harver Dzodin看过小方的作品,非常果断地说:“他是中国的卡帕。” (作者系解放军报高级记者、第九届长江韬奋奖长江系列获得者)